“样板戏”的岁月
来源:
时间:2015-05-05 12:00:57
“样板戏”于文革期间正式命名,始作俑者是康生。
我接触“样板戏”较早,在其未冠名之前,就看过好几出。1965年我大学毕业后,即被分配到河北艺术研究所,后又参与河北省艺术学校的筹建工作,再后来又担任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的主要领导工作,并与“样板团”的一些演员多有交往。可以说,我与“样板戏”厮守大半生,不仅从其起源、发展、兴旺、寂寞,再到今天的复兴,历经了“全程”,而且亲历、亲闻了诸多“样板戏”排演期间的奇闻轶事。面对近年来一些剧团由唱“样板戏”选段,到复排上演全出,难以名状的心绪时时萦绕心头,脑际间不由涌现出当年排演“样板戏”的一幕幕情景。
“样板戏”于文革期间正式命名,始作俑者是康生。1966年11月28日,在中央文革召开的万人参加的“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会”上,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宣布: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海港》、《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等8部文艺作品为“革命样板戏”,这8个演出团体为“样板团”。这是“样板戏”一词的最早出处。不过,将《红灯记》称为“样板”,时间更早一些。1965年春《红灯记》到上海演出,3月16日的《解放日报》就发文称《红灯记》是“一个出色的样板”,但这时还没有“样板戏”的称谓。1966年至1967年,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样板戏”的演出更为红火,“样板戏”一词出现的频率更高,几乎充斥了全国的报纸、传单、造反小报和广播。
1967年5月,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8个“样板戏”全部调进北京,举行“革命样板戏大会演”。两报一刊大力宣扬,既发文章又发社论,还发表了江青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座谈会上的讲话《谈京剧革命》,将“样板戏”的宣传推向了极致。1967年第6期《红旗》杂志发社论《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称:“京剧革命,吹响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样板戏”“不仅是京剧的优秀样板,而且是无产阶级的优秀样板,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各个阵地上‘斗、批、改’的优秀样板。”
现在人们口头说起抑或当年报刊上宣传的“样板戏”,笼统地称“八个样板戏”或“八大样板戏”,但究竟是哪“八出”却说法不一。当时“官方”“钦定”的“八出”,即康生宣布的那“八出”,是第一种“版本”;第二种“版本”是1995年2月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八大样板戏(珍藏本)》一书,该书刊出的“八出”是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海港》、《龙江颂》、《奇袭白虎团》,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并将京剧《平原作战》和《杜鹃山》作为“附录”刊后,示意《平原作战》、《杜鹃山》不在“八大样板戏”之列;还有一种“版本”是将《杜鹃山》、《平原作战》和钢琴伴唱《红灯记》也列入“八大样板戏”……名目繁多,众说纷纭。
我感到,在“八大样板戏”是哪“八出”问题上,之所以出现提法上的差异,是因为看这些剧目的角度不同。康生宣布那“八出”时,是在1966年11月,当时有些“样板戏”还未出台,当然他不会提到,这是从时间上说的;后来又出现了几出,如《龙江颂》、《杜鹃山》,其影响远远超过交响音乐《沙家浜》,所以现在人们提到“八个样板戏”,就很少涉及交响音乐《沙家浜》了。
戏剧界对“八大样板戏”的说法,有个不成文的“共识”,即认为按时间顺序上说,康生说的那“八出”,是“第一批样板戏”,而在1970年以后出现的京剧《龙江颂》、《杜鹃山》、《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以及《红嫂》、《磐石湾》等,称为“第二批样板戏”。不过,平心而论,在这第二批中,除《龙江颂》、《杜鹃山》的水平和影响尚可与第一批比肩外,其他几个就逊色多了,有的甚至已被观众遗忘。比如说京剧《平原作战》,表现的是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思想,主题是积极的,但那些剧情都是从人们耳熟能详的电影《平原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的有关情节中拼凑起来的,没有什么新意,人物形象也干干巴巴。只是主要演员李光(扮赵勇刚)、李维康(扮小英)、高玉倩(扮张大娘)有上乘的表演,成为“人捧戏”,才使该剧有了一些影响,及至后来又由中国京剧院复排上演。这次复排演出,我从电视转播上看过,从唱念到表演,都是一种模仿,较之“李光版”差了一大截。通观“样板戏”的称谓,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即30多年来,“样板戏”一词只见于领导讲话、报刊发文和口头流传,而正式出版的“样板戏”剧本、舞台演出字幕和“样板戏”电影字幕上,均称“革命现代京剧”和“革命现代舞剧”,而从不用“样板戏”一词。也就是说,在这些地方还保持着一定的严肃性和科学性。我在河北省艺术学校工作多年,师生们演出“样板戏”时,我常和教务处的同志商量,咱们的字幕上就写“革命现代京剧”和“河北梆子现代戏”,不要用“样板戏”一词,因为“样板团”演出时的字幕上也不写“样板戏”。多年来省艺校就这样做了。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样板戏”作为中国的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其普及程度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1967年5月1日,“八个样板戏”齐聚北京举行大会演直到6月中旬,历时37天,演出218场,观众达33万人。当时看“样板戏”,是我供职的戏研室的一项业务,也是政治任务,自然对这次大会演特别关注。单位领导派我提前到北京买票,戏票搞定后再招呼同事们赴京观看。当时戏票非常难买,天不亮就得到位于前门大栅栏的一个售票点排队,长长的队伍拥挤不堪,临到窗口时挤得喘不过气来,若非年轻力壮绝不能胜任。拼死拼活总算买到了两场票,后又通过“样板团”的朋友搞到几场,才松了一口气。这样,会演中我一一看了《红灯记》、《沙家浜》、《海港》、《智取威虎山》。记得在看中国京剧院的《红灯记》时,开演前主要演员一律着戏装站在台上,手捧《毛主席语录》贴在胸前,和观众一起唱《东方红》,唱毕才开戏。戏结束时,主要演员又带妆站在台上,在强烈的音乐伴奏下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反复唱,直至目送观众退场毕,演员才退回后台卸妆。这种做法影响到全国。当时省会石家庄演“样板戏”时,也大都这样做,很多时候演员不仅高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目送观众退场,有时还手拉手把观众送出场外,然后才回去卸妆。北京的这次会演,影响极大,6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观看了《智取威虎山》,6月18日《人民日报》发社论,发出了“把样板戏推向全国去”的号召。全民开始学唱“样板戏”,上至耄耋老人,下迄几岁的孩童,不论有嗓无嗓,不论五音全不全,大都能照猫画虎地唱出几段“提篮小卖拾煤渣”、“临行唱妈一碗酒”、“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我家的表叔数不清”等等。甚至连《沙家浜》中戏极少的配角沙四龙那四句〔西皮快板〕“四龙自幼识水性,敢在滔天浪里行”,许多人也学唱不误。至于《沙家浜》中胡传魁唱的〔西皮二六〕“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在车间地头更是随处可闻。可以说,“京剧样板戏”全民大普及的程度,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形成了一种罕见的文化现象。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大普及,在工农兵群众中还真出现了一批好演员,后被选拔到专业剧团。业内人士都知道,剧团的演员讲究幼工,京剧演员一般十二三岁进戏曲专科学校“坐科”八年,打下扎实的唱、念、做、打基功,演唱风格上还要分“流派”。然而,从工农兵中选拔的演员,仅是凭着一条好嗓而来,没有幼工,更无“流派”可言,进剧团后只好补学身段表演;因其进团时大都在20岁上下,有的已近30岁,重学武功已不现实,只好在身段表演上修修补补。当然也有出类拔萃的。
在全民大唱“样板戏”的同时,全国范围内的专业剧团又大办“样板戏学习班”,地方剧种的剧团纷纷组建“移植学演样板戏”的机构,就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歌舞团也以维吾尔歌剧形式移植了《红灯记》。这样的移植机构全国计有数百个,仅河北即有33个之多。当年,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移植的河北梆子《龙江颂》因突破唱腔设计禁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成为该院的保留剧目,社会影响很大,至今舞台上还常演出江水英的唱段。石家庄市丝弦剧团移植的《智取威虎山》,保定地区老调剧团移植的《红灯记》,邯郸地区平调落子剧团移植的《红色娘子军》,唐山市评剧团移植的《智取威虎山》,当年我就看过多次,也都有一定的水平,至今印象很深。
1970年夏天,我参与河北省艺术学校的筹建工作。到正在省梆子剧院座谈、搞方案。至年底很快就开学了。12月28日新生入学那天当晚,开“迎新晚会”,男孩子们唱“临行喝妈一碗酒”、“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早也盼,晚也盼”;女孩子们唱“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八一三,日寇在上海打了仗”,不仅是那么个味儿,而且连行当各自也已选定了。戏曲班的100多名孩子,大都来自农村,入学前就都能唱两口,可见当年“样板戏”在农村的普及程度。当时我兼上文化课,教材也是清一色“样板戏”剧本。先后给学生讲了《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剧本。公正地说,在学演“样板戏”的热潮中给学生讲“样板戏”剧本,这对进一步加强学生对剧情和唱词的理解是有帮助的。
京剧、河北梆子班的老师,大都是老教师,许多人过去又是著名演员,教“样板戏”虽说是个“新活儿”,但他们提前学一步,就算“现趸现卖”,教起学生来也得心应手。在我的办公室兼排戏课堂上,我常常是一边办公,一边听著名京剧演员刘会琦老师给京剧班学生教唱《沙家浜》选段。她按照洪雪飞的唱腔,一丝不苟地教练,仅“授计”一场中阿庆嫂的那段(二黄慢三眼)“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就教十天半月的,抠得极细,就像现在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每晚的“跟我学”节目一样。京剧班老师教《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完全按照“样板戏”的标准曲谱;河北梆子班老师照省梆子剧院移植的梆子曲谱,不走样地教唱。学生进展都很快,也培养出不少著名演员,而今活跃在舞台上的京剧演员张艳玲就是这一届的毕业生。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其后的两三年内,戏曲院校的教学上,戏曲舞台上,仍是以“样板戏”为主,“传统戏”只是偷偷地开放。当老师们拿出劫后余存的靠旗、马鞭、厚底靴,学生们像见到“出土文物”一样的惊诧。1979年2月5日至22日我到北京参加全国艺术教育会议时,许多省市的戏校领导还在私下互相打问传统戏教学在整个教学中所占比例问题。会后传统戏教学逐渐开放,戏曲舞台上的传统戏也逐渐上演了,“样板戏”热开始降温。
一出戏的剧本,是剧作者完成的一度创作。至于剧本怎样处理,音乐怎样设计,演员如何表演,舞台怎样装置,那属于二度创作,都是根据剧团的实际情况和演员条件而定,不同剧团和不同的演员在同一个剧本的处理上往往是不一样的,也不可能完全一样。比如京剧《玉堂春》,梅程荀尚四大流派都擅演,但风格各异。在《起解》一场中,这四派均唱“苏三离了洪洞县”,而张派却唱“低头离了洪洞县”。行家、观众不但不认为“张派”“不标准”、“走了样”,反而感到这是不同流派的不同特点。再如同是演“水浒戏”中的林冲,京剧演出戴“倒缨盔”,而昆曲演出却戴软罗帽。观众一看这不同的盔帽,不用听唱腔就分清了剧种。我们看到的大批传统戏,正是因为遵循了艺术规律,尊重了不同流派的特点,才有了戏曲舞台上的流派纷呈,异彩多姿。
这种情况不必扯得太久远,就是“样板戏”确立之前的同一剧目,也允许有各自的唱念做打和舞台调度。这里只说后来极尽红火的《红灯记》。这出戏的题材来自于电影文学剧本《自有后来人》,许多戏曲剧团争相以此为题材编演现代戏。1965年我曾在邯郸看过河北梆子剧院的《红灯记》,高明利扮李玉和,齐花坦扮铁梅,路翠阁扮李奶奶。这出戏的唱念与后来的“样板戏”大不相同。记得李玉和被捕后在狱中有一(安板)段唱:“老人家莫要悲痛莫心酸,报仇雪恨总有那一天。”铁梅在狱中也有一(二六)段唱:“抬头望断南飞雁,低首思亲眼望穿。”这些虽无豪言壮语但充满深情厚意的唱段,优美而深沉,后来在按“样板戏”重新移植后,不复存在了。
本来,各剧种不同版本的《红灯记》,按自己的条件和风格演出着,就很好,但自京剧《红灯记》“钦定”为“样板戏”后,各剧种必须照此移植,而在移植过程中却严重地破坏了艺术规律,有的甚至还因此带来种种灾难。对于学习移植“样板戏”,1971年初的《人民日报》和《文汇报》都明示“地方戏曲移植革命样板戏是一场革命”,要求各地方剧种“在‘样板戏’创作原则指导下,对自身的剧种艺术进行革命化的改造”。并严格规定,学演必须“不走样”。上海越剧院排演《龙江颂》时,于会泳就指示:“词儿一个也不能改,调度一点也不能动,就是唱腔用越剧的,其他都要按京剧原样来演。”有了“不走样”和“按京剧原样来演”,各地方剧种不得不违背自身的剧种特点,使地方戏难以发挥自己的唱腔特点,甚至有的变得不伦不类。在以“样板戏”创作原则“对自身的剧种艺术进行革命化的改造”的指令下,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只好对原来演出成功的《红灯记》推倒重来,按照“样板戏”的模式重新移植。表演上还好说些,按“样板戏”的路子走就是了,但唱腔却是个难题。因为河北梆子唱腔和京剧唱腔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声腔体系,“不走样”实在难办。音乐设计人员只好按照梆子的板式硬套:京剧若是〔导板〕,梆子就用〔尖板〕;京剧若是〔散板〕,梆子也用〔散板〕;京剧若是〔西皮三眼〕,梆子就用〔大慢板〕。在节拍上,京剧若是4小节,梆子必须也是4小节,不得越雷池一步。要达到这样的效果,设计人员只好掐着秒表来设计唱腔,不能长,也不能短。这种设计方式,现在听来很可笑,但在当时却是很严肃的政治任务。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束缚了创作人员的创作才能,而且设计出的唱腔总带京剧味。这也是把戏曲唱腔“政治化”带来的恶果。当时,有一位在唱腔设计上造诣很深的专家气愤地说:音符有什么阶级性,哪个阶级的音乐不都是1、2、3、4、5、6、7吗?这样的言论必然招致祸灾,遭到批斗。
在“不走样”的艺术桎梏下,排演“样板戏”的演职员人人自危,生怕在哪个关节上,一不留神儿出现差池而招来祸端。比如《红灯记》中李铁梅穿的上衣是什么颜色,打了几块补丁,补丁补在什么地方,有多大面积,各剧团、各剧种的李铁梅的上衣,必须完全一样,否则就是“破坏‘样板戏’”。1974年,河北省艺术学校京剧班师生排演了第二批“样板戏”中的《杜鹃山》,在农村和石家庄多次演出。有一次在石家庄演出,我负责“跟幕”,亲睹了舞台工作人员风声鹤唳的紧张情状。这出戏的第四场叫“青竹吐翠”,剧本中关于这一场的布景提示是:“新竹泛绿,青翠欲滴;杜鹃盛开,绚丽多彩……”舞台队的一位极细心的老教师,因多次观摩过“样板戏”,记下了舞台上的许多细节,这次演出她回忆起“样板戏”《杜鹃山》布景上的杜鹃花是54朵,生怕我们学演的《杜鹃山》“走样”,开演前她就急匆匆地在台上一朵一朵地数,看是不是54朵。数的结果是54朵,她才长长吁了一口气。其实,李铁梅上衣的补丁补在哪儿,有多大;杜鹃山上的杜鹃花有多少朵,完全可以依据演员的身材和舞台的大小而定,没有必要这样严苛。再者说了,《红灯记》剧本关于剧中人服饰提示上,并没注明必须是多大的“补丁”。补丁大是穷人家的孩子,补丁小也是穷人家的孩子;《杜鹃山》剧本关于布景提示上也只说“杜鹃盛开,绚丽多彩”,也没注明必须是多少朵花。54朵花叫“绚丽多彩”,53朵也可叫“绚丽多彩”。这就像传统京剧《空城计》中诸葛亮所用的“城楼”,不同剧团演出时大小、高低各不同,不也很好吗?话是现在这么说,在当年是万万不可出此言的。
在文革那样的特殊年代,无论是排演“样板戏”,还是移植“样板戏”,因稍有不敬的言论或“走了样”的舞台演出而被扣上“反对‘样板戏’”罪名的情况,多有所见所闻。东北某市有个京剧团演《红灯记》,演到第六场“赴宴斗鸠山”,剧本规定情景是:日本宪兵队的伍长将李玉和拉下去受刑,但李玉和宁死不讲,伍长复上场后向鸠山道:“报告,李玉和宁死不讲!”鸠山道:“宁死不讲?”伍长:“队长,我带人到他家再去搜!”鸠山:“算了。共产党人机警得很,恐怕早就转移了。”可能是由于扮演伍长的演员过于紧张,他复上场后说成了:“报告,李玉和招了!”扮鸠山的演员一听满拧了,但他很机灵地来了个“救场”:“招了?不可能吧?算了……”演出结束后,扮伍长的演员以“破坏‘样板戏’”罪名被定为反革命,遭长期批斗。应该说,扮伍长的演员是严重的失误,但“鸠山”的“救场”已经“救”过来,接受教训也就是了,不至于被打成“破坏‘样板戏’”的阶级敌人遭批斗。上海郊县的一位乡间戏曲艺人,因学演“样板戏”时加进了一些“噱头”笑料,即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处*。北京有位舞蹈专家,在为“五七干校”学员排演《红色娘子军》时,因舞台小,难以按“样板戏”的原样排演,只得将舞步稍加改动。就这么一点改动,竟被扣上“破坏革命样板戏”的罪名,对之进行残酷迫害。
不过,在“天高皇帝远”的情况下,出现对“样板戏”不恭的表现,也就无法问咎了。冀中蠡县爱唱戏,文革时许多村镇仍有民间剧团,当时也只能演“样板戏”。记得1968年春节村里来了潴龙河南岸某村的一个剧团,头天晚上演《沙家浜》,演胡传魁结婚那场戏时,竟增加了一个打扮妖冶的女子舞着绸子满台跳舞;胡传魁和刁德一也不知穿的什么部队的服装,两个人还都戴着眼镜,他们可能认为凡大官都戴眼镜吧。念白是满口蠡县话,至于低八度的唱腔更听不出哼的什么。第二天晚上演《红灯记》,所有演员的服装都是农民常穿的衣裳。李奶奶、铁梅穿什么,戏装和农民衣裳不好分也就罢了,这还能凑合,但也让日本宪兵队的侯宪补穿着农村男式对襟小棉袄,留着寸头,不戴帽子,脖子上围着白毛巾,左腋下还夹着一个60年*公用的硬纸板做成的文件夹,这就有点不伦不类了。——这样学演“样板戏”,如在城市必然会被抓起来,但在穷乡僻壤却安然无恙,老百姓看后一笑也就拉倒了。
当年坊间还有一些传闻,说来也很有意思。如说某剧团演《智取威虎山》时,第六场“打进匪窟”,剧本规定是——座山雕:“脸红什么?”杨子荣:“精神焕发!”座山雕:“怎么又黄啦?”杨子荣:“防冷涂的蜡!”扮演杨子荣的演员可能由于太紧张,这段对话的台词变成了——座山雕:“脸红什么?”杨子荣:“防冷涂的蜡!”座山雕一时没反应过来,照问不误:“怎么又黄啦?”扮演杨子荣的演员一听,第一句说错了,又不能收回,遂改口现编词儿:“又涂了一层蜡!”另据闻一个剧团演《红灯记》,在“刑场斗争”一场,铁梅在监狱中见到了李玉和,李玉和即按剧本唱道:“有件事几次欲说话又咽,隐藏我心中十七年。我……”这时铁梅打断李玉和的唱,应急忙说:“爹!你别说了,您就是我的亲爹!”据传扮铁梅的演员看到台下有某大人物看戏,紧张过度,竟说成了:“爹!您别说了,我就是您的亲爹!”这些带有某些调侃的“版本”之所以在群众中广泛流传,或者是由于“不许走样”原则搞得演员非常紧张,把台词说错了,这就是人们生活中常说的“越怕越出错”;或者是观众出于对“不许走样”文化禁锢的不满而演义出来的。



 揭秘末代皇帝溥仪贩卖故宫国宝惊人内幕
揭秘末代皇帝溥仪贩卖故宫国宝惊人内幕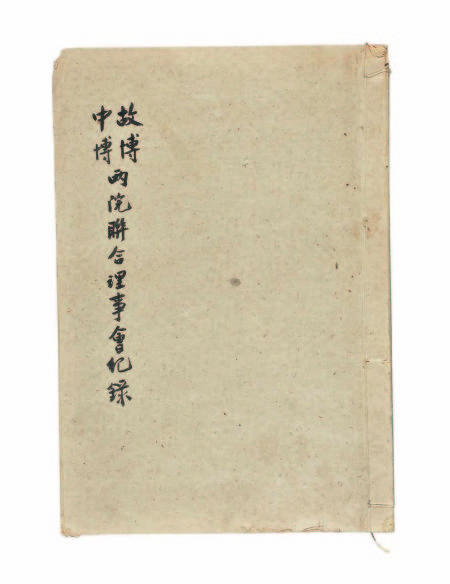 中国嘉德2015春拍:信札中的故宫文物南迁
中国嘉德2015春拍:信札中的故宫文物南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