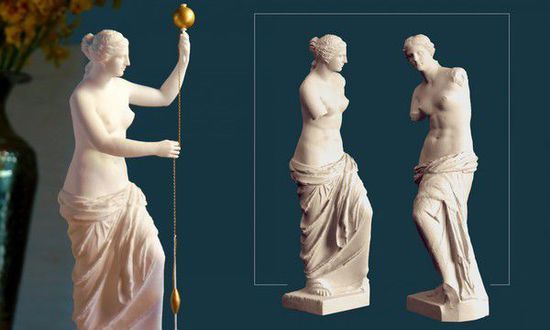莎士比亚戏剧的当代诠释
来源:
时间:2015-06-16 11:25:50
哈姆雷特离开我们已经太久了,人们把他悬挂在半空中,好像他生来多么高贵,让他像一个披着满头假发的家伙在台上乱嚷乱叫,让那些只爱热闹的低级观众听了出神。
1990年,林兆华导演《哈姆雷特》时,曾在演出说明书上写下这样一段话:“哈姆雷特离开我们已经太久了,人们把他悬挂在半空中,好像他生来多么高贵,让他像一个披着满头假发的家伙在台上乱嚷乱叫,让那些只爱热闹的低级观众听了出神。现在,我们要让他回到我们中间来,作为我们的兄弟和我们自己。”林兆华希望莎士比亚走下神坛,摘掉假发、假鼻子,洗掉浓妆, 成为我们的同代人,而他的作品《哈姆雷特》却被视作“离经叛道”,好评寥寥。
十五年过去了,第八届上海国际小剧场戏剧展演中马俊丰导演的《理查三世》里仍有这样的台词:“我不喜欢这样的表演,我不喜欢假模假样的哈姆雷特或者罗密欧与朱丽叶。”有专家批判“这是在糟蹋莎士比亚”,以致“愤怒”的导演不得不喊出“希望莎剧专家别来看我的戏”。十五年了,中国都不知有多少个旧貌换新颜了,为何戏剧界却仍在纠缠同样一个问题,使它依旧成为导演创作时无法摆脱的梦魇?那么问题便来了,如何才是不糟蹋莎士比亚?
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还是留待专家来解释。我仅就这次国际小剧场戏剧展演中的两个中国莎剧,吕岩执导的上戏表演系12级实习大戏《仲夏夜之梦》、马俊丰执导的《理查三世》谈谈粗浅的看法。
莎士比亚自被引入中国以来,一直拥有崇高的地位,但却似乎并未成为新时期导演的自觉选择,或许只有每每到节庆时才会涌现一大批应景的莎剧作品,如轰轰烈烈的1986年中国莎剧节、1994年上海国际莎剧节,包括近两年为庆祝莎士比亚诞辰450周年连番上演的莎剧。究其原因,或许辽远的故事与诗化的语言是横隔在莎剧与二度创作者中间很大的障碍。在找不到灵感时,有些导演完全按照原剧硬导,莎剧诗化的台词从并不那么理解其意的演员嘴里朗诵出来,不走心却还要装腔作势地摆出一些姿势,让观众昏昏欲睡,简直可以称为灾难。当然,这一点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彼得·布鲁克在谈到英国当时已经僵化的莎剧演出时也强烈地批判过这一点。受杨·柯特(Jan Kott)1964年出版的《莎士比亚,我们的同代人》影响,布鲁克找到了在当下导演莎剧的灵感,那即是将莎士比亚与我们的时代平行,并用当代剧场的方法(重新考察阿尔托、梅耶荷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格洛托夫斯基、布莱希特的论断)与形式(空的空间)来导演属于当代人的莎剧。《仲夏夜之梦》(1970年,舞台剧)、《李尔王》(1971年,电影)使彼得·布鲁克名声大噪,并深刻影响了各国导演呈现莎剧的方式。而这些思想也成为中国自林兆华以来许多见识过西方当代剧场的导演们的共同意识,尤其是近几年,这样的意识更为自觉。从这个角度来说,吕岩与马俊丰都是站在莎剧与现代人的关系角度来诠释他们的作品。
在当代看莎剧,最有吸引力之处便是看每个导演对于它的不同诠释。而这事实上是在看导演自己生命的房子,房子的宽度、厚度、高度、间数、材质决定了他/她对作品诠释的独特视角、丰富程度、人文情怀、美学标准与哲学高度,也决定他/她将用哪些技术手段来呈现自己的诠释。中国的莎剧很长一段时间被用来呈现人文复兴式的“人”的精神的复苏。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于莎剧的诠释也开始展示其丰富性。
吕岩这出《仲夏夜之梦》最有趣的诠释便在于将四个青年男女的相互追逐视为一场战役,这也是当代人看待爱情的独特方式。赫米亚一改原剧中千金大小姐的娇羞,当她发现拉山德情移海伦娜时,竟痛苦地与海伦娜厮打在了一起。而拉山德与狄米特律斯为抢夺海伦娜,把海伦娜的鞋都抢掉了,一人抱住海伦娜的一条腿,迫使海伦娜上演高空劈叉的惊险动作。对深爱的人目不转睛,对单恋自己的人却冷若冰霜。两性关系是亘古不变的永恒话题,而将其处理成为妙趣横生的“战争”场面却是导演的匠心独具。正因为有此构思,服装设计上采用了带有军装迷彩的元素,演员在上戏花园里追逐仿佛置身于丛林一般,与整个舞美设计也相得益彰。
《仲夏夜之梦》的另一个亮点便是梦幻的舞美设计,导演将之称为造梦,用上戏四月的美丽校园作为舞台,配以多媒体、灯光与轻纱漫布,充分使用假定性原则,试图给人一种置身于仲夏夜花园的错觉。然而除了给观众营造梦幻的视觉,给演员提供表演场所以外,这些舞美设计是否成为建构人物关系不可或缺的符号(并非锦上添花而是非如此不可)?另一方面,对四个年轻人的精彩诠释是否延续到剧中其他人物关系中去?仙王、仙后、扑克戏班子是否在导演同一个诠释体系里发生共振?导演对于表导、舞美都很有想法,但在呈现上基本还是属于如实搬演,并未对这个戏有一个总体的诠释,更未像彼得·布鲁克那般通过将仙王仙后与人间的两对情侣互为镜像而将整剧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虽有精彩与亮点,却并未将之连成整体,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马俊丰的《理查三世》是一出解构的戏剧,他称刚开始阅读《理查三世》时找不到灵感,感觉像是一出宫斗戏,毫无深度,不知该如何诠释。在他心里,如果找不到自己作为导演想说的话还不如不做这个作品。然而有一天当他处在半梦半醒的状态时,突然找到了灵感。理查三世对权力极大的欲望与当代人贪得无厌的欲念不是很相似吗?只不过满足欲望的路径不同。于是,这个戏切入点有了,接下来的一切迎刃而解,舞美设计、台词的选择、动作的选择便围绕了欲望的操控与被操控展开。马俊丰的剧组成员少而精,演员只有一个——2013年上戏表演系毕业的谷京盛,舞美徐肖寰是近年来频有佳作的优秀设计师,制作人丁盛有颇深的戏剧理论造诣,这样一支精干的队伍时时与导演碰撞出火花。
由于有了清晰的主旨,马俊丰这出《理查三世》最大的亮点便是与主旨有关的意象与动作的选择。一开始进场观众便是被控制着入场的,入场后,第一个意象是一张餐桌,上面摆满了食物,还有各种各样的张开的断手。演员独坐一角,头发散乱,看上去疲惫、衰老而又错乱。随着演出的进行,象征安夫人的酒瓶意象出现,被理查三世操控着演了一出偶戏;理查的脑袋钻过桌上的洞与自己的手对话,被自己的手殴打、操控;理查操控着观众,跟他演了一段拙劣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理查靠在人群里喃喃地独白;理查钻到桌底下;理查倒立……演员在空间里快速地腾挪,从一个动作到另一个动作,观众的视线也被牢牢吸引住,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他接下来说什么、做什么。当理查喃喃地说着“当140岁的理查送走139岁的理查,当139岁的理查送走135岁的理查”时,观众不免被这位泯灭人性、诡计多端的暴君寂寥的内心独白打动。
导演对空间的把控、对演员的调动的能力都值得称赞。然而,莎剧里呈现欲望或欲望的操控与被操控的作品也已经很多了,为何非要用《理查三世》来说话?《麦克白》、《亨利六世》、《安东尼与克利奥佩特拉》等许多莎剧里都涉及了欲望。是否稍微调整一下意象和动作,这出戏就可以换其他名称来演出了呢?换句话说,为什么非《理查三世》不可?这或许就是导演需要进一步思考或者正在思考的问题。什么东西是非要用理查三世的故事来诠释的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回到文本是必要的,然后从文本投射在内心的倒影里提炼出这个非如此不可的主旨与形式。解决了这个问题,接下来再进行意象和动作的再次选择与规整。
如果说诠释是导演的工作,那么这出戏成败与否很大一部分还是要看演员的演绎。而无论在《仲夏夜之梦》还是《理查三世》,我们都看见了演员,以及演员的身体。
在表演上,如何处理好莎剧大段诗化的台词一直是颇让演员头疼的事,一旦处理失当,便会成为演员在舞台上朗诵,甚至被批评为不说人话,而难以与观众产生共鸣。而由于莎翁在中国的崇高地位,随便删改台词也一度被认为是大不敬的事。当代国外导演在演出莎剧之前,都会根据当下的语言习惯做一个自己的翻译演出本,其删改程度之大胆也是有目共睹。在吕岩的这一版《仲夏夜之梦》中,他最先带领演员做的功课便是修改剧本,保留剧中诗意的语言,并加入现代人理解的新元素,如热门时事、网络用语,只有让演员充分领会莎士比亚的精神,并说出让他们自己最舒服的台词,他们的表演才有可能打动观众。于是,在这次演出中,语言不再成为阻隔演员与真实的表演之间的屏障。当语言通畅了,演员的身体也不再那么僵化了,变得灵动而有爆发力。该剧中的四个主要演员樊轶宁、全思颖、顾珂嘉、曹泽昊的表演可圈可点,让人印象深刻。《理查三世》里谷京盛的表现也让人眼前一亮,他是一位非常能理解导演意图并有自己独立思考的演员,《理查三世》里充分展示了他身体上的各项素质,极度的投入与专注、通透的声音、身体的反应与塑型能力。
余秋雨在2013年将1983年出版的《戏剧理论史稿》命名为《世界戏剧史》重新出版,在序言里写道:“记得我在两度颁奖的时候,都断定它很快就会被同类新书追赶、超越、替代。但是三十年过去,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偶然也会在传媒间看到一些艺术争论,似乎很激烈,却是前人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完美解决了的,而且解决的等级远远高于今天的争论,我在书里详细写过。但大家都不知道,好像世界刚刚诞生,历史刚刚开始。这种状况,显然比我们的年代,显得更加愚昧无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不可以说没有被糟蹋的莎士比亚,只有诠释得好或者不好的莎士比亚,如果人们能体会到这两个问题的不同,那我们这十五年、这三十年也算没有白过。



 揭秘末代皇帝溥仪贩卖故宫国宝惊人内幕
揭秘末代皇帝溥仪贩卖故宫国宝惊人内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