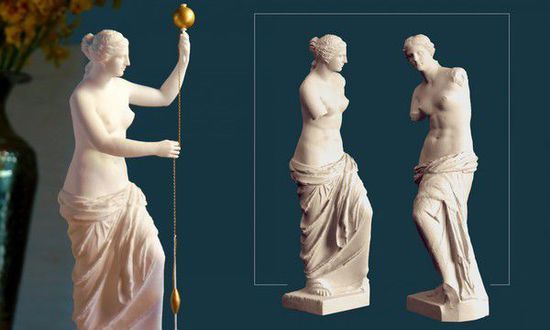道情又称“拉波戏”
来源:
时间:2015-06-12 09:56:10
道情在民间又称“拉波戏”,在古代则称为道歌,最初是传道者宣传教义和募捐化缘的说唱艺术:由云游道人拿上尖板渔鼓演唱。

声名赫赫的秦腔、委婉动听的眉户戏,都是陕西的“流行曲”。但当岁月的箫声逡巡而过,曾如秦腔、眉户一样流传于此的悠悠道情,却离我们越来越远。道情在民间又称“拉波戏”,在古代则称为道歌,最初是传道者宣传教义和募捐化缘的说唱艺术:由云游道人拿上尖板渔鼓演唱。后来传于民间,才形成一人唱、众人和的坐唱形式。而经过长期演变,如今一些地区的道情逐步成为演唱有故事情节的剧目,还配有皮影戏。
近两年,周至道情、临潼关中道情皮影戏、长安道情陆续拿到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入场券,引起了不少人对道情这一民间艺术的关注,但这并没有扭转它的整体命运,受现代生活节奏和娱乐方式的冲击,如今西安一带的道情生存环境正日渐缩小。
存在了一千多年的道情社
我们对道情的探寻,从离市区最远的周至县开始:经历2个半小时的高速公路行程抵达周至县城,记者一行仍需要再在同行的周至文化馆周主任“右拐左拐再左拐……”的不断指引下,驱车在乡间村里行进半个多小时,才算到达此行的目的地——周至县楼观镇军寨村的一个农家小院。
军寨村是一个只有600多人的小村庄,但传说中,离这里不远的楼观台就是道情的发源地,而这里,也存在着周至如今唯一的一个活体道情社。楼观镇文化站站长张德文告诉我们,被申报非遗的周至道情,就是此地的“军寨道情社”,“社里如今有十几位老人,都在村里住着”。一位中年男子这时骑上辆自行车出了小院,叫人去了,张站长说,那是军寨村的村支部书记杨战林,他已经过世的父亲,也是道情社的一员,而他本人则是如今道情社的社长,也是最年轻的成员,“他也会唱,但主要还是做一些组织工作,管管社里的资金。你们真要听,还是得听老人们的”。
由于一些成员外出或下地干活,除了杨战林,我们只采访到了道情社的陶宏德、李效林、李效荣、以及周至道情传承人陈德荣四人。这些已经六七十岁的老人们或许因为平日没事,大家都会聚在一起练练唱,嗓音保持了特有的洪亮,而说起军寨道情社,63岁的陶宏德很是自豪,颇有点“咱家这是根正苗红”的意思,“周至县志在公元423年就有军寨道情的记载了。这个社存在了一千多年,道情曲也是从一千多年前传下来的,不容易啊!”
老人们回忆自己当年学道情,已经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事情,“我们的师傅都是一个人——道情社里上一辈的能人杨八爷,那时跟他学道情戏的都是村里十几岁的娃,因为反正也不读书,更没有电视电影看,整天闲在家里,听道情戏就是最流行的娱乐方式,而学成了道情戏,可就是村里受欢迎的文艺青年了!”李效荣口中这位杨八爷的“官名”,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但他却记得杨八爷对弟子是来者不拒的,“只要是村里有兴趣学道情的,都可以跟着他学”。
尽管如此,学道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陈德荣回忆当时一起学戏的十几个孩子里没几人识字,“要硬生生记大段大段的唱词,而道情的曲更是没有书面记谱的,完全靠口传心授,学起来很是艰难,可没人放弃,学了十几年,大家总算把八爷传下来的十几个本折戏和十几个调学了下来,没把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丢了”。
伴奏乐器声音可传至1公里外
由于社员们年纪都比较大了,李效林说如今道情社只有在过会或是有红白喜事邀请的时候“正式唱一下”,在我们的不断“撺掇”下,老人们决定现场演出经典道情戏《卖道袍》的其中一段。为表正式,他们甚至找出了一个在记者眼里足以号称文物的唱道情的主要伴奏乐器——一个据说从清代甚至更早年代流传下来的老渔鼓。
当古老打击乐器响起,这个长约四五尺的筒状乐器在李效荣的击打和拍奏下发出“噌噌”、“嗡嗡”、“嘭嘭”的响声,而伴随这样的响声旋律,“主要演员”陈德荣开始如痴如醉地演唱,虽然只是坐唱,没有更多华丽的舞台动作,但从他声腔里发出的浑厚却不失婉转的嗓音,清雅而高亢,足以打动人心。记者尤其陶醉于道情的和声部分——当众人为陈德荣和音时,简直堪比最美妙的混音效果。据说,好的渔鼓虽然貌不出众,但是在一定范围内距离越远听得越清晰,声音可以传至1公里地外。这话也许是真的,因为当老人们开唱不久,我们很快发现小院门口挤满了一群好奇的“小脑袋”。
西安的戏迷可能更熟悉、也更习惯于欣赏秦腔和眉户。但在李效荣眼中,道情自有它独特的魅力,“道情既有秦腔的板腔体成分,也有眉户的连曲体成分,而且唱词朴实、通俗。”老爷子说道情也是“优雅戏”。
西安群艺馆非遗保护部主任王智告诉记者,由于早年一般是民间道人进行传唱,其游走性质,让道情流传各地而且形式上大同小异,之所以又各有细微差别,则是与当地方言及地方小曲的唱腔有所融合的结果,比如在陕西一些地区的道情就融入了秦腔的因素,而陇东道情同当地的皮影戏相互融合,已形成著名的陇剧。又如河南坠子的形成,亦是道情与其地民间曲种合流的产物。
军寨村的村支部书记杨战林则告诉记者,道情的唱词从古至今也有不少变化,从“传道专用”的讲述升仙道化的传统道情,演变到如今有不少歌者自己创作新唱词。他边说,边给记者展示了军寨道情社新创作的《十唱建设新农村》,“还没来得及排,准备眼下就开始练了”。
道情在陕西有三个“黄金期”
离开周至,记者一行又辗转来到位于长安区韦曲北街的长安区剧团(原长安县剧团),在大门口,打听家住此处的长安道情代表性传承人之一的王昭玺的具体住址,简直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刚问了一句,正看别人下棋的一群人纷纷指起路来,有位大爷在指路后很自然地加上一句,“你又是哪个电视台的吧?”看来,这位采访对象是这一带的名人。
从1958年起在长安区剧团做秘书兼任艺术股长的王昭玺,相比周至的“陈德荣”们的“实践型”,是“研究型”传承者——他通过数十年的搜集整理,完成了《长安道情音乐》两册书。
虽然并没有考证到是否道情真的从周至楼观台起源,但王昭玺认为早在唐代,道情开始进入一个全面兴盛期。“唐朝大诗人韩愈的《华山女》中,就描述了中唐时期,佛教和道教宣教唱对台戏的热闹景象,吕纯阳、钟离权等道教徒留下的‘结交常与道情深,日日随它出又沉’等诗句,更可见当时京城内外宣讲道情的盛况。唐诗后几卷也有道情词。”此外,他还提到了唐朝《续仙传》的记载:“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蓝采和手持拍板(简板),唱踏歌行乞于市。’这可能是对早期道情的最具体的描写了。”
此前名不见经传的民间小调突然成了举国追捧的“流行乐”,王昭玺分析可能因为当时的皇帝唐玄宗李隆基重视道教,并将其奉为国教,一时道教大兴引发的。“虽然兴盛从唐朝起,道情的形成年代也许更早”,西安群艺馆非遗保护部主任王智也曾对道情的源头有过追寻,他提供了《西汉演义》第三十回中,张良在街头扮作乞丐教幼童们唱道情的故事情节,用以佐证自己的猜测。
而杨战林对道情的辉煌记忆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那时道情可是火得很,几乎天天晚上社员们都会在村里唱戏,就在这个院子,每天挤得满满登登全是人。”他说,逢年过节时,村里街坊更经常席地而坐,敲起渔鼓、简板,拉起丝弦,一唱唱到深夜。
王昭玺还补充了道情的另一个“黄金期”——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全国“小戏汇演”“新剧汇演”前后,“当时的陕西省戏曲学校专门设立了道情班,聘请民间老艺人为学生传授道情演唱技艺,还创作改编演出了许多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新剧目,比如《剪红灯》《山花姑娘》《墙上记帐》。1959年省戏曲学校道情班和长安县剧团将道情搬上大舞台,改编排演了《隔门贤》《墙头马上》”。
如今,西安人最熟悉的道情曲目可能仍是《隔门贤》——上世纪80年代,省戏曲研究院青年团曾晋京汇报演出的这部道情戏引起了广泛好评。但少有人知的是,省戏曲研究院的《隔门贤》,就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临潼道情老艺人李世忠向长安县文教局传授剧本和曲谱,再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由长安县剧团的王昭玺和其他几名老艺术家传给研究院的。
年轻人对道情越来越陌生
临潼的道情戏因为融入了皮影因素,显得格外不同,而家住临潼区海家庄、已经60岁的卢学林老人就是临潼“关中道情皮影戏”的传承人,也是前文所提的李世忠老人唯一的徒弟,提到道情现状,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一些稍微会点的年轻人平时都打工去了,逢年过节能组织起来就很不容易了。现在我有二三个老伙伴帮忙,但是能演出道情皮影戏的老艺人就剩了我一个,表演的时候一个人要负责6种乐器,生旦净丑也是一人唱,我现在最害怕想的是,我一旦不在人世了,临潼道情皮影戏是不是就真的消失了。”
那么在道情最早的出处——道观,现在还能听到道情吗,王昭玺面对记者的提问摇摇头,说至少自己没有找到,“我去年还专门去了楼观台,今年初去了八仙庵,可是能唱出《道藏》里二三十首道情的道徒几乎已经无人”。有意思的是,王昭玺甚至在八仙庵碰到了一个以前跟自己学艺的学生为游客“客串表演”,“不是道士,却在里面领头唱曲呢”。
已过75岁的王昭玺因去年担负了长安区剧团新编大型道情戏《祥云谷》的几乎全部作曲工作,引来不少媒体追逐,但他自己却对出名有点无奈,“不是我一个老头子非要逞能,当时在咱这真是找不到第二个人能干这个事(为道情编曲),剧团的年轻人连道情是什么都还不知道,是编好曲以后,我和我的一个学生用了一个月时间,手把手再教会他们唱的。”老人苦笑着摇摇头。
王昭玺说,虽然《隔门贤》如今在戏曲研究院生存得还算不错,但他觉得城里的小娃娃把这个戏总演得不太好,“他们经历的太少,而且似乎总唱不出以前走街串巷的老艺人能唱出的人情味。这只是在吃一部老戏的本”,有意思的是,军寨道情社几位看过《祥云谷》的老人们也对王昭玺的这个作品提出了类似的异议,“赶不上道情老调儿的原汁原味,曲子有点太新了,秦腔味也有些重”。
传承令人忧心忡忡
对更多城里人而言,如今军寨的猕猴桃远比这里的道情出名很多——这里是全国有名的猕猴桃种植基地,150多户村民家家都种植猕猴桃,在采访的时候,陈德荣的小孙子不停地“猴”在爷爷身边,“奶奶让你去给桃套袋子呢!”老人开玩笑地做势要“揍”孩子,却也叹息着,“过去生活单调才去学道情,现在的娃们又要念书,又要挣钱,哪有时间和精力学道情呢。”虽然如今民间仍有一些道情爱好者,比如周至现在有十来个中年人在学习道情,但其“业余性”以及人数之少让道情老艺人很担忧。“周至县剧团都没有道情戏的排演”,军寨道情社的老人们说,在成为“非遗”以后,大家演出仍是在邻近的几个村子。“也许是离省城太远了吧,这里道情的名气传不出去,也没谁想来学”。
比军寨道情社情况好些,临潼的关中道情皮影成为“非遗”后,卢学林名气大了不少,“不在村里表演了,一般省里或者市里接待外宾、大型活动或者艺术展演的时候才去”。可是他却多了另一份苦恼,“那些外宾和观众只把道情当稀奇看。而不是曲艺艺术”。此外,卢学林也越来越为一件事忧心,“虽然已经是‘非遗’,仍没有年轻人找到我,说愿意学它。我们几个老人年纪大了,记性越来越差,如果不能传承,申遗时做的很多前期准备工作不是就白费了。”他很焦急,“我是不会用网络,不然真想在网上发个消息,看哪家的孩子真的喜爱这门曲艺,愿意学,我可以免费教他。”
现有艺人年龄偏大,部分艺人离世,导致道情曲牌、唱腔已濒临灭绝。传承,成了每一个受访者无一不忧心忡忡地跟记者反复提到的一个词。
长安区剧团团长郑志军曾是王昭玺的学生,当时剧团排《祥云谷》,他是希望道情可以以此活起来,“如果没有唱道情戏的新人,没有剧目的不断创新,怎么叫算作真的活?”而现在长安、周至、临潼道情社除了传承人难觅,面临的共有问题就是经费紧张,“没有资金,怎么教授年轻人道情戏,将其传承下去?”
王智告诉记者,道情的发展史承载着我国民间音乐、戏曲艺术、乡俗礼习、宗教文化等多学科的衍变信息,具有重要的艺术科学研究价值,但让他遗憾的是,“在我们因道情申遗搜集资料时,在西安并没找到系统研究道情艺术的专业学者”。而关于传承问题,王昭玺倒有个自己的想法:“农村的很多媳妇都在家闲着,有些人对道情也很喜爱,可以问问她们想学吗。以前有手艺传男不传女的说法,但是现在能让后人仍能听到道情,显然更重要。”



 揭秘末代皇帝溥仪贩卖故宫国宝惊人内幕
揭秘末代皇帝溥仪贩卖故宫国宝惊人内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