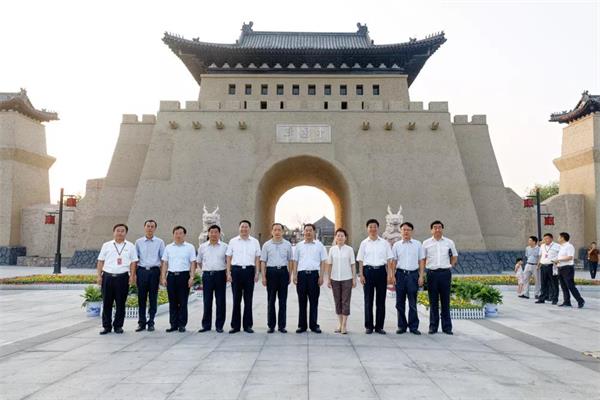读彼得·汉德克|语言在小说中的边界
来源:
时间:2019-10-17 09:34:06
奥地利小说家、戏剧家彼得·汉德克语言在小说中的边界——读彼得·汉德克小说集《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肖星晨瑞士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

奥地利小说家、戏剧家彼得·汉德克
语言在小说中的边界——读彼得·汉德克小说集《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
肖星晨
瑞士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2019年10月10日下午,瑞典文学院揭晓了2018年和2019年的两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中,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奥地利小说家、戏剧家彼得·汉德克。汉德克最被中国人所熟知的是他早期的剧作《骂观众》,以及由他编剧、维姆·文德斯导演拍摄的电影《柏林苍穹下》。

《骂观众》剧照

电影《柏林苍穹下》剧照
在《骂观众》和《柏林苍穹下》中,汉德克在不同艺术形式中所表现出来的实验性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样的实验性也反映在小说集《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中。就像诺贝尔文学奖写给汉德克的授奖词一样——“凭借着具有语言学才能的有影响力的作品,探索了人类体验的外延和特性”。在汉德克的这本小说集中,无处不体现出他对“语言”和“人类体验”这两者关系的思考。

《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彼得·汉德克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出版
《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这部小说集一共收录了汉德克的四篇小说,包括两个中篇小说《推销员》和《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与小说集同名),两个短篇小说《监理会的欢迎词》和《一个农家保龄球道上有球瓶倒下时》。早在2016年拜访中国时,汉德克就在演讲中谈到自己“痛恨‘讲故事’”,因此这四篇小说都遵照他的艺术追求,对情节描写刻意淡化,而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小说的语言上。
比如《监理会的欢迎词》,这篇较早写作的小说虽然还未完全摆脱情节,却已初现语言实验的端倪:小说的内容是一篇某代表的发言,叙述的核心本应该是欢迎词的内容,却变成了门卫儿子的意外死亡事件,因为叙述者的注意力总是不自觉地滑向它。小说语言像一棵树一样,沿着突然出现的分叉不断蔓延下去——门卫寻找孩子的故事、来听报告的先生们在路上遭遇的故事,在“报告”这棵大树上都是相互分离的枝桠。不过相互分离的故事又在破碎的叙述中产生了交叉,来听报告的先生们与农夫、门卫及门卫的儿子因为“报告”联系在了一起。这些故事在叙述中突然以片段式的方式插入,又以孩子的死为核心层叠交织。作者以杂乱无章的语言,消解了表达的有效性。而贯穿整个叙述的,叙述者对于暴风雪所造成的威胁的关注,揭露出隐藏在语言背后,叙述者频繁的心理活动。因此,在叙述者的语言和所欲表达的内容之间形成了一种错位:所说无法表达所想,这种错位的张力在结尾处爆发,使得叙述陷入了一种无言的境地。
从滔滔不绝到无言,小说读者可以感觉到,在汉德克的小说中,语言不再是陈述情节的工具,小说的主角变成了语言。这同时也体现出作者对写作的认识——语言的边界就是写作的边界。
这种语言上的实验在《推销员》和《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显得更为大胆。这两篇小说都是以传统谋杀故事为模仿对象创作的“伪”谋杀故事,因为在这两篇小说里,揭露凶手不再是推动叙述发展的动力。
在《推销员》中,具体人物几乎都不存在了,遑论寻找凶手这一特殊人物。所有的人物都以“他”“她”“她们”来命名,唯一有身份的人物——“推销员”,他的身份也不是实指,而是一种隐喻,喻指能够出现在各种场合却又不参与其中的外来者。而在《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中,虽然出现了人物,但作者根本就没有设置悬念——凶手的凶杀过程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而这个“重大事件”只占用了一小段云淡风轻的叙述。之后凶手游荡到边境小镇,经历了一些和之前的凶杀毫无关系的事情,小说便戛然而止了。
汉德克的意图很明显:故事不是需要关注的,如何在叙述中使用语言才是。
因此在《推销员》中,每一节小说都采取了两段式的写作方式。在第一段中,他采用元小说的叙述方式,刻意暴露出作者的创作意图——对传统谋杀小说叙事技巧的理论综述。例如从整体上,他把传统谋杀故事的情节推进动力总结为有序和无序的交替,而秩序感的产生来自于对事物的叙述方式,即对语言的使用方式。所以在第二段中,叙述方式摆脱了传统故事的逻辑,在一个个毫无关系的意象和场景的拼贴中,读者感受到如同观看快速变换的蒙太奇画面的头晕目眩感,作者对“周围所有那些平平常常的事情不厌其烦地一一枚举”,改变了语言在日常被使用时的空间感和时间感。在这种使用语言的方式下,比如他在小说中反复提到的“鞋子”这一意象,“鞋子”二字已经丧失了它所指的“鞋子”这件物品的本意,变成了有序或无序的一个符号。语言丧失了原本所要传达的意义,汉德克还原了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的符号性本质。
同样的,《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关注的也不是谋杀,而是主角布洛赫的心理状态。在这里,“谋杀”的情节成为了工具,目的是造成布洛赫的这种焦虑乃至失常的精神状态。在逃亡中,他越来越频繁地感到作为形式的语言和它所指的内容无法成为一个整体。“他依次看到一个‘柜子’,‘然后’‘一张’‘小’‘桌子’,‘然后’‘一个’‘纸篓’,‘然后’‘一块’‘窗帘’。”但他重新打量这些物体时,所看见的“桌子”“床”都用绘画符号代替了。汉德克通过对布洛赫精神状态的描述,唤醒读者对语言和所指这对看似理所当然的组合的重新思考。
翻译者韩瑞祥在为小说集所写的前言中的评价中说,“语言与感知之间的危机始终伴随着小说的叙述”,在汉德克的小说中,对于语言在小说中所能达到的边界的探索构成了他的作品本身。这使得他的作品拥有了先锋的姿态,呈现出探索本质的勇气。
来源:中国艺术报
比如《监理会的欢迎词》,这篇较早写作的小说虽然还未完全摆脱情节,却已初现语言实验的端倪:小说的内容是一篇某代表的发言,叙述的核心本应该是欢迎词的内容,却变成了门卫儿子的意外死亡事件,因为叙述者的注意力总是不自觉地滑向它。小说语言像一棵树一样,沿着突然出现的分叉不断蔓延下去——门卫寻找孩子的故事、来听报告的先生们在路上遭遇的故事,在“报告”这棵大树上都是相互分离的枝桠。不过相互分离的故事又在破碎的叙述中产生了交叉,来听报告的先生们与农夫、门卫及门卫的儿子因为“报告”联系在了一起。这些故事在叙述中突然以片段式的方式插入,又以孩子的死为核心层叠交织。作者以杂乱无章的语言,消解了表达的有效性。而贯穿整个叙述的,叙述者对于暴风雪所造成的威胁的关注,揭露出隐藏在语言背后,叙述者频繁的心理活动。因此,在叙述者的语言和所欲表达的内容之间形成了一种错位:所说无法表达所想,这种错位的张力在结尾处爆发,使得叙述陷入了一种无言的境地。
从滔滔不绝到无言,小说读者可以感觉到,在汉德克的小说中,语言不再是陈述情节的工具,小说的主角变成了语言。这同时也体现出作者对写作的认识——语言的边界就是写作的边界。
这种语言上的实验在《推销员》和《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显得更为大胆。这两篇小说都是以传统谋杀故事为模仿对象创作的“伪”谋杀故事,因为在这两篇小说里,揭露凶手不再是推动叙述发展的动力。
在《推销员》中,具体人物几乎都不存在了,遑论寻找凶手这一特殊人物。所有的人物都以“他”“她”“她们”来命名,唯一有身份的人物——“推销员”,他的身份也不是实指,而是一种隐喻,喻指能够出现在各种场合却又不参与其中的外来者。而在《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中,虽然出现了人物,但作者根本就没有设置悬念——凶手的凶杀过程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而这个“重大事件”只占用了一小段云淡风轻的叙述。之后凶手游荡到边境小镇,经历了一些和之前的凶杀毫无关系的事情,小说便戛然而止了。
汉德克的意图很明显:故事不是需要关注的,如何在叙述中使用语言才是。
因此在《推销员》中,每一节小说都采取了两段式的写作方式。在第一段中,他采用元小说的叙述方式,刻意暴露出作者的创作意图——对传统谋杀小说叙事技巧的理论综述。例如从整体上,他把传统谋杀故事的情节推进动力总结为有序和无序的交替,而秩序感的产生来自于对事物的叙述方式,即对语言的使用方式。所以在第二段中,叙述方式摆脱了传统故事的逻辑,在一个个毫无关系的意象和场景的拼贴中,读者感受到如同观看快速变换的蒙太奇画面的头晕目眩感,作者对“周围所有那些平平常常的事情不厌其烦地一一枚举”,改变了语言在日常被使用时的空间感和时间感。在这种使用语言的方式下,比如他在小说中反复提到的“鞋子”这一意象,“鞋子”二字已经丧失了它所指的“鞋子”这件物品的本意,变成了有序或无序的一个符号。语言丧失了原本所要传达的意义,汉德克还原了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的符号性本质。
同样的,《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关注的也不是谋杀,而是主角布洛赫的心理状态。在这里,“谋杀”的情节成为了工具,目的是造成布洛赫的这种焦虑乃至失常的精神状态。在逃亡中,他越来越频繁地感到作为形式的语言和它所指的内容无法成为一个整体。“他依次看到一个‘柜子’,‘然后’‘一张’‘小’‘桌子’,‘然后’‘一个’‘纸篓’,‘然后’‘一块’‘窗帘’。”但他重新打量这些物体时,所看见的“桌子”“床”都用绘画符号代替了。汉德克通过对布洛赫精神状态的描述,唤醒读者对语言和所指这对看似理所当然的组合的重新思考。
翻译者韩瑞祥在为小说集所写的前言中的评价中说,“语言与感知之间的危机始终伴随着小说的叙述”,在汉德克的小说中,对于语言在小说中所能达到的边界的探索构成了他的作品本身。这使得他的作品拥有了先锋的姿态,呈现出探索本质的勇气。
来源:中国艺术报



 潘鲁生:始终如一的守护与传承
潘鲁生:始终如一的守护与传承 冯骥才:中国文化正在粗鄙化
冯骥才:中国文化正在粗鄙化